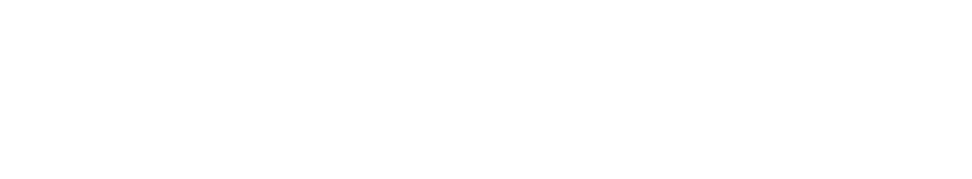清晨,在半梦半醒间,有鸟鸣,婉转动人。时而如儿时的清脆的竹哨,时而似悠扬低回的管箫,时而如幼儿园阿姨那婆娑的手鼓;时而几声急促的叽喳如清泉入渊,间或一声稍长的呼唤如晨光般丝滑.循着声音,我知道鸟儿在枝头上回眸、在青草间低头、在玉兰连理处滑过靓丽身影——哦,这是我心灵的交响曲。
我舍不得睁开眼睛,感受窗台流过的一丝清凉,不确定自己躺在窗内的卧榻,还是窗外的草地,让这清凉扶过我全身,让尘世里每一点亢奋都渐渐平伏;然而一睁开眼,窗外是一幅兰色底的画儿,那兰似深海之水,剔透,灵动,那浅浅的疏影也随这流动而缓移莲步……
我不禁责问自己:你到底错过了怎样一个春天啊!
是啊,唯有失去能告知你可贵,提醒你珍惜,这晨曦中的一梦竞让我生出好多好多不舍,好多好多记忆的残垣断壁。
记得浦口也有鸟儿叫。19舍后山有一片竹林,刚进校时才种上,一杆一杆都整齐地插在土里,即使那儿也有。一年后竞争扎出或稀稀疏疏或密密麻麻的漫山小竹子,也有“竹林笋儿高过母”的,不过极少。再过一年,竟蔚然成林,衬着沿山的一片绿悠悠的草坪,偶尔生起的薄雾,还有一条小路通到林子里,再通到山的另一边,还有那棵叫不出名字的郁郁如华盖般撑在这小径旁的大树。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就由这小路在宿舍和自习室间来来回回,由春走到夏,又走到秋,又走到冬。等到一夕秋凉时,麻雀就成了群,和明湖、星湖那边的麻雀连成了片,在风起风住间群起群落,在冬日临近的日子里炫耀生命的蓬勃。
在我这个山城儿子的眼中,那山实在是极小,但我在心底喜欢叫它“山脉”,因为它蛮横地横梗在宿舍与教学楼之间,成一个绵延南北走向的长条状。那片竹林只占据了它的南段,北段却有一片树林,树枝仿佛水墨画里一般,深黛,遒劲。那里的鸟儿种类更多了,羽毛更鲜亮,有的还有极大极漂亮的翅膀。当那些大鸟在高高的树枝间滑翔的时候,他们的尾羽也会展开,我想,这应该是它们最得意的舞姿了。自然,这里的鸟儿有更丰富动听的歌声,他们是不屑和山那边的麻雀一较高低的,他们自有他们的对手。旁边就是“力行馆”,这里是展示南大学生展示才艺的舞台,有时能听到少女练歌的咿啊声,或许在某个宁静而明媚的午后,还能听到有人练习钢琴,在盛大的节日里又是人生鼎沸,欢歌如潮。在顶不住诱惑的日子里,我也在这里学过两支拉丁,那一年盛大的社联晚会上,我的拙劣舞步有同班的男生捧场。
关于鸟儿的话题,有时候也带着滑稽。就在我入学的那年,据说有人亲眼看到一只野鸡一样的东西一头扎在西平的外墙上,死了!它最终没能如“南大霸气狗”和“北大学术猫”那样出名,但却时常被我想起,因为我时常想起西平。想起西平的白墙灰瓦在阳光照射下别有韵味;想起西平园内有70岁的盛奶奶安置的“爱护草坪”的警语;又想起某人在这里开着空调的自习室里睡着的情形;又想起某人在那里呆坐了一下午,书还只翻了一两页的情景;甚至想起那个大得有些奢侈的男厕所。
浦园的草坪很多,也很美。草坪常常配上各色的花和树,譬如大平台那里有柏树作篱,拐角还有龙爪槐,还结过籽;明湖周围的草地上有不少马褂木和合欢树,合欢的花絮如丝,红润而又繁盛,映红了天也铺红了地;星湖边是垂柳,偶尔也见到各色的月季,最难得是还有一个码头,夏夜里可以临风扶柳,诗意就来了,醉意也来了。这些景致都给南大草坪增色不少,然而也不知是那位妙人心多了一窍,就在明湖外面设了一个鸽子房,这一家子人丁兴旺,使得从校园大门,到明湖,到南平,到星湖,甚至于到了西平,这一线上都有鸽子的身影。鸽子咕咕的叫声和噗噗的拍翅声都是很能宁神的节奏;他们又喜欢在星湖外边草地上形成的一个水洼附近嬉戏,我也喜欢;它们一点不怕人,在男孩子风驰而过的自行车轮旁边悠然踱步;我甚至看到过他们偷吃南平园里一种红豆灌木的种子。
当然了,鸟儿们绝对不会忽略一个地方。中央大道的尽头有一喷泉,站在这里往右看,有一个条小路向山坡上蜿蜒,路边一堆几杆竹影,掩着一块石碑,上书“名人园”。好了,这里没法说了,漫山是全球文化教育界名流手植的各色名贵花木,一年四季有几枝花开,有几双璧人,有几声鸟鸣。这样的景致,佛语有过精当的评价“不可说,不可说,一说既是错”。
天已经大亮了,窗外南园依旧鸟鸣。在北京毕设的两个月里,我错过了在南大最后一个春,错过了草长和莺飞,才明白即将失去的东西多么宝贵。回想去年这个时候,在北园的长凳上,漫不经心地享受无数个这样的早晨和流光溢彩的傍晚,伴着这花香鸟语,这天籁梵音,参悟人生,又何须暮鼓晨钟。
南大,放飞的风筝永远回不来了,他不舍,也要飞,也要想做一只美丽的鸟儿。但请你抓住他的一线脐带,永永远远不要放手,不然他飞不高,飞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