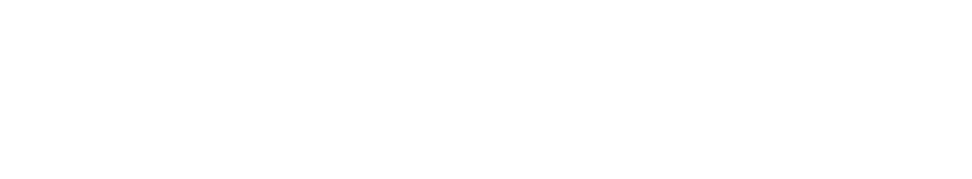清明假期,买了二两新茶.于茶道,我并无多少了解,也无心做一个茶博士,好在人前卖弄.我喝茶,也无甚讲究,只是从小喝惯了茶水,闻惯了茶味,略觉得比时兴的各色饮料来的爽口,来得平淡.
前一段时间,囿于实验室项目进度和硕士开题,转博的压力,整日过得浑浑噩噩,忽略了季节的变换,忽略了亲朋的联络,更谈不上喝茶、冥想这样悠哉的乐事了。及至今日下午两点,从京郊学术交流回来,有些疲惫了,且放纵自己偷这半日清闲吧。夕阳斜照,在地板上描着长长的蟹爪兰的影子,两只草金鱼在这闲暇的日子里也懒懒地嬉戏于碗莲叶间,我想泡一壶茶,享受这似曾相识的温暖,和平静。
翻了一翻,发现居然仍留着去年一点铁观音,颜色还那么绿,只是所剩不多,也差不多碎了,将近一半都成了细末儿。我拿了一张干净的纸,轻轻地把尚算得上茶叶的那一部分碾出来,拿水冲了。嗯,还有些香气。我于是开始享受自己这种小情调,享受这种从碎茶叶里淘茶喝的老习惯,享受那些像茶水一样清淡又余香悠然的过往。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是不喜欢喝茶的,因为那时农村喝的都是坨茶,都特别苦。说是茶叶,却掺有不少被切成小段的茶树枝,而且每次喝茶都从茶坨上一点点掰下来,都碎了,泡出一缸碎叶子碎梗子,一不小心就能吃进嘴里。这样的茶,只有老人们喝,工匠们喝,干重体力活的男人们喝。因为它便宜,买一坨回来,掰一小块,拿了大号的瓷罐子,可以泡上一整天;又因为它生津解渴,天然健康,地里的农夫们,石匠们,砖瓦匠们,全靠它补充烈日头下流失的水分。我的爷爷是一位老道的匠人,手艺齐全,技艺精湛,会做竹货;会开山取石;会锯木头弹墨斗;会捡土瓦盖屋檐儿。他喝了一辈子的茶,到老了,就离不了了。在家里一个人喝,赶场天就到街上的茶馆,约上三五老友,须发皆白,摆了长条凳,围了一张八仙桌,开始吹牛。吹儿子媳妇儿,吹孙男孙女,吹时下年轻人的轻浮,吹当年的老规矩,吹燕儿冲张家新盖的洋楼几楼一底,吹枣子坡王家扒手儿子入了狱。
我是爷爷的幺孙,是所有孙子辈里唯一一个睡爷爷的床长大的,俗称是李家湾李云甫的尾巴,和这个地方上别的老头儿的尾巴一样,是最受老一辈宠爱的。这个尾巴可以吃到很多姥子(姑妈)叔伯孝敬给婆婆爷爷的吃食,还可以经常跟着去赶场,吃街上卖的零食。爷爷宠我,喜欢带我去街上玩,饿了就给我买零食吃,渴了就给我喝盖碗的沱茶,混到太阳上了西山梁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就踩着田埂间的石板路回家。
我于是也慢慢习惯了喝苦沱茶,习惯了天天给爷爷泡苦沱茶。爷爷也渐渐老了,去赶场的时间也少了,只能在家喝茶。每到周末,就陪爷爷喝茶,早上泡一壶,下午换一壶。爷爷一边喝茶,一边盯着我写作业,看书,学打算盘,甚至也学一些他早年从旧学堂里学来的,学校早就不教的东西,我已经不对那些在他脑子犹疑了一个甲子的知识的正确性抱太大幻想。爷爷训诫得最多就就是要学“文质彬彬”,莫学“挑兮达兮”,却从不教我家传的竹篾手艺。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总后悔让自己的一众儿孙学手艺挣饭吃,决心不能再害了这个幺孙。如果他老人家泉下得知自己最疼爱,最引以为傲的幺孙现在的状况,是否会有一丝欣慰,或者是遗憾?
后来,我考上市里著名的高中,又上了大学,爷爷的坟上也渐渐青草葱茏起来。再不喝苦沱茶了,有一段时间我特别醉心于龙井的飘逸唯美。看那些嫩芽在嫩绿色的茶水里舒展,沉浮,飘逸;品那种淡淡的,似有若无的甘冽。及至偶尔喝了一次铁观音,终于觉得,茶,还是味道重一些的,更适合我;及至今日喝了这陈年的铁观音,终于觉得,茶,还是碎一些的适合我。这样的偏爱,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我的血液。离了这点土气,我也不再是我,不再是李家湾李云甫的尾巴儿。
呷了最后一口茶,醒一醒神.我倒掉了泡过得茶叶,涮洗茶缸,融入这京城的暮色中,准备明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