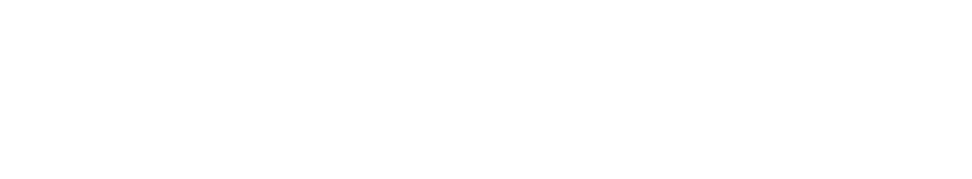最近,我读了理查德·费曼口述的《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译者在序言中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促使我一口气读完了全书。
他们说道:
“这不是一本关于天才的书,连同前一册《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是一本关于真实的书——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好奇、真实的为学,真实的做人:只不过拥有这些的正巧是个天才,一个由真实而得的天才。
在中国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上,有人文,有技术,却偏偏没有科学。有技术的原因是我们有技术的精神——把任何东西变成实用;没有科学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科学精神——由天真的好奇出发的寻根究底,探求真实原本。
中华民族是最信奉实用主义的,而且常常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它浸透了我们文化的每一根经纬度:从孔子的实用主义理论,到走了原样的实用主义佛教,到精粹专集的实用主义政治学《资治通鉴》。我们历史上的成功在于实用主义,而近代与现代的失败也在于此。因为没有求真的指南,实用主义的强大蒸汽机便把整列火车推向了不明方向的去路。
费曼的故事有的生动幽默,有的深情感人。但是它们背后的含义却都很有份量。或许,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也是我们所急需和必须的。”
我觉得他们说的中肯而不失力度,一语言中中国科学乃至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追求经世致用,却并不关心真理。或者说,中国人心目中的真理仅仅是一种处世方法,能够让自身生活的更加充裕,舒适。中国人不关注那些大而空泛,形而上学的问题,诸如宇宙的演变,生命的起源。中国人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并不过分在乎历史的真相;中国人发展航空航天技术是为了强我国防,保卫家园,而并不迫切想利用这些技术探索未知领域。
辜鸿铭先生说,中国人的精神,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温驯顺服。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人缺乏批判精神,反抗精神呢?自古以来,我们习惯于接受一个人的统治,这个人是皇权;我们习惯于服从一种声音的支配,这种声音叫专制,为了生存安全,我们宁可放弃自由,甚至渴望平庸。中国人向来害怕成为少数派,不敢标新立异,因为少数派很难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社会舆论的理解支持。记得大学时,每次作业,大家都要互相参考,充分讨论,防止和大多数人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最后的作业都是一个版本衍生出来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在蔓延,那就是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总是安全的,起码不至于太糟糕。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绝对是缺乏独立精神的中国人的创造。
有时,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现在中国四处捐钱,做好事却鲜有朋友?中国人留给别人的印象是狡诈,涣散,没有骨气,并且一直难有改变?其实,根本原因是我们在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上没有与时俱进,与世界同步,我们的国家倒在这点上成了少数派,变得异乎寻常的独立了。我们动辄显摆自己开放的姿态,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开放的胸怀。
最近,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之余,关于大学精神,校庆本质的讨论也尤为热烈,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的批评。听到批评,主流阵地就不干了,就拿出清华的辉煌历史和显赫功绩回应,还有甚者纠出批评者的不堪往事嘲讽一番。我觉得,这是最有辱大学精神的,批评之声无论对错,出发点是好是坏,我们若能包容,总能把它转化为对未来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反思式的庆典正如阴雨天的烟火,不也别具特色吗。好吧,不这样做当然也没有问题,可是总得允许有人这样提议吧。大学是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学直接输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下大学精神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国民精神。大学之大,应该是大公民之大,而不是泱泱大国之大。如果说比之早前大学精神确有缺失,我觉得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是治学精神。没有治学精神,大学便没有真正的输出,一切都是引进,拿来,消化的好,是大杂烩,消化不好,就成了垃圾场。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一个民族源源不断的输出精神财富,大学从不隶属于哪个主义,评判大学好坏的标准是其创造力和引领风范。纵观世界,优秀大学的办学策略并无一定之规,但其办学宗旨却有相似之处,这些优秀的大学必脱离主义的束缚,政治的干扰,方能真正优秀起来。
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所说: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所以,大学从不应该为一党一派服务,而应该始终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财富,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一个人若没有这种精神气质,很难有真学问,也不会有引领时代进步的勇气。然而很遗憾的是,纵观当代中国大学的校训校风,能够彰显这种胸怀的几乎绝迹。即便是这样的现状,依然会有大批捍卫者、鼓吹者和追随者,他们出于利益、无知和怯懦,这是最不令人奇怪的事。时至今日,王国维纪念碑文读来仍令人振聋发聩:“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世界注定是要更加多元化的,未来也必将是一个大公民的时代。治学精神就是一种倡导思想多元化的精神,有人捍卫无知,就必须有人勇敢质疑。我们曾经过度狭隘的理解并实践了实用主义,导致我们偏执的给和谐号提速,却忘记了文明号,冷落了进步号。然而,实用主义最最核心的东西恰恰是变通,没有理由表明我们就当如此,别无他途。倘若我们也要输出有影响力技术、学说、制度、思想,我们就要修炼内功,欲修炼内功,须从重拾大学之治学精神开始。